归途,一场流动的炼狱
北上的T16次列车,比来时更加拥挤。李明盛没有再花钱去换一个靠窗的位置,他被挤在一个三人座的中间,左边是一个体味浓重、鼾声如雷的壮汉,右边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,孩子时不时会因为燥热而啼哭。过道上,空气中,都塞满了归乡或再次外出闯荡者的疲惫与茫然。
这节车厢,就像一个流动的炼狱,将他重生以来所有的骄傲和体面,都按在地上,用最粗糙的方式反复摩擦。
来时,他觉得这人间烟火充满了机遇和生命力,因为那时的他,自认为是俯瞰众生的神。此刻,他只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窒息和疲惫,因为他终于意识到,自己不过是这芸芸众生中,最狼狈、最可笑的一个。
他的身体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,只能随着火车的节奏,麻木地摇晃。他没有再拿出任何书籍,也没有再思考任何关于未来的宏伟蓝图。他的大脑,像一台被病毒攻击后,删除了所有核心文件,只剩下最基础操作系统的电脑,一片空白,一片死寂。深圳那几天的经历,像一场高烧,烧尽了他所有的狂妄、激情和自以为是,只留下一具虚弱的、需要重新学习如何呼吸的躯壳。
他把自己蜷缩在狭小的座位上,闭上眼睛,试图用睡眠来逃避。但在嘈杂的环境和纷乱的思绪中,他根本无法入睡。各种声音,像无数根针,刺入他敏感的神经。
右边孩子的啼哭声,让他想起了自己上一世那个刚刚出生的儿子。他记得自己当时也曾手忙脚乱,笨拙地学着换尿布、冲奶粉。那时的他,虽然也为未来焦虑,但内心深处,有一种作为父亲的、最朴素的责任感。而这一世,他满脑子都是帝国和革命,却从未想过,未来他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父母,如何组建一个家庭。他所谓的成功,从一开始,就抽离了最基本的人性温度。
左边壮汉那如雷的鼾声,和身上浓重的汗味,让他想起了梁浩那粗鄙却生机勃勃的“烧鹅饭理论”。他开始明白,自己一直以来所追求的,是一种纤尘不染的、存在于商业计划书和PPT里的精英式成功。他鄙视一切与泥土有关的东西,鄙视汗水,鄙视粗俗,鄙视那些为了生存而奔波的原始欲望。而现实给了他最响亮的一巴掌:恰恰是这些他所鄙视的东西,才是构成这个商业世界最坚硬的底座。
他开始了一场无声的、对自己的审判。羞愧、愤怒、恐惧、迷茫,四种情绪,像四匹野马,在他的内心世界里疯狂地冲撞、撕扯。
羞愧于自己的无知与狂妄,竟然妄图用一本未来剧本去挑战整个时代的运行规律。
愤怒于自己的愚蠢与懒惰,竟然轻易地抛弃了上一世赖以成功的、最宝贵的品质——脚踏实地。
恐惧于未来的不确定性,当金手指失灵后,他发现自己在这个时代,可能连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都不如,因为他的心态,已经被彻底腐蚀了。
迷茫于脚下的路,他不知道回到那个熟悉的校园后,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室友,如何面对那些曾经被他轻视的课程,如何重新开始。
火车在某个小站短暂停靠。一个背着巨大帆布行李包的民工挤了上来,因为没有座位,就近蹲在了李明盛的脚边。那是一个看起来比李明盛大不了几岁的青年,脸上却刻满了与年龄不符的沧桑,双手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和裂口。
青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、已经干硬的馒头,就着一瓶浑浊的白开水,大口地啃了起来。他吃得很香,仿佛那是人间美味。
“兄弟,你也回北方?”青年看李明盛一直盯着他,主动搭话,口音带着浓重的西北腔。
李明盛木然地点了点头。
“唉,今年这活儿不好干。”青年叹了口气,拍了拍自己腿上的灰尘,“在东莞一个工地上干了三个月,最后老板跑路了,工钱都没拿到。没办法,只能先回家了。”
他的话语里,充满了失望,但眼神里,却没有绝望。
“那你……接下来打算怎么办?”李明盛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。他觉得,自己此刻和这个被欠薪的民工,在某种程度上是同类,都是被现实痛击过的失败者。
“回家呗!还能咋办?”青年咧嘴一笑,露出一口被劣质香烟熏黄的牙,“回家帮俺爹把秋收了。地里还有几亩玉米,收了能卖点钱,好歹能让婆姨和娃,过个好年。等开春了,再出来找活干。人嘛,活人还能让尿憋死?”
他看着李明盛,见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,便以一个过来人的口吻劝道:“兄弟,我看你像个学生娃,白白净净的。是不是在外面遇到难事了?没啥大不了的。天塌下来,都得先填饱肚子。肚子饱了,才有力气想别的。俺们这些出门打工的,就信这个理。”
“天塌下来,都得先填饱肚子。”
这句最质朴、最粗糙的话,像一道电流,猛地击中了李明盛麻木的神经。他看着那个民工,第一次,发自内心地,对一个社会底层的人,产生了一种近乎敬畏的情感。他意识到,这些看似平凡的人们身上,蕴藏着一种他早已丢失的、最强大的力量——那就是脚踏实地、坚韧不拔的生存智慧。
火车继续前行。李明盛没有再说话,但他内心的坚冰,已经开始出现裂痕。他将上一世和这一世的自己,放在天平的两端,进行着残酷的对比。他终于承认,那个中了彩票般的重生者李明盛,在心性上,远不如那个在地下室里啃着馒头、熬夜学习编程的前世李明盛。
他正在进行的,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重生逆袭,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自我毁灭。想通了这一点,李明盛的后背,瞬间被冷汗浸透。
他将这次南下之旅,当成了那个“投机者李明盛”的葬礼。当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站时,他感觉,那个旧的自己,连同那些被撕碎的商业计划书一起,永远地留在了南方那座喧嚣的城市。走下火车的,是一个全新的、一无所有的李明盛。
当李明盛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,推开宿舍302的门时,已经是深夜。
宿舍里,只有王涛一个人还在电脑前,聚精会神地打着《星际争霸》。屏幕上,无数的狗和地刺正在围攻人族的基地。张伟和赵鹏都已经睡了,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。
“我操,明盛,你回来了!”王涛被开门声吓了一跳,回头看到是他,惊讶地叫道,“你小子跑哪去了?请了快一个星期的假,手机也呼不到人。辅导员都快把电话打到你家去了!”
“……家里出了点事,已经处理好了。”李明盛撒了个谎,声音因为几天没好好说话而显得异常沙哑。
“没事就好。”王涛没有多问,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看你这脸色,跟挖了七天煤一样。赶紧洗洗睡吧。”
“嗯。”
李明盛放下背包,从里面拿出几件脏衣服。他没有立刻去洗漱,而是站在宿舍的中央,环顾着这个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。他感觉,自己和这个充满着青春荷尔蒙和简单快乐的宿舍,隔着一层无形的、厚厚的玻璃。
第二天,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愈发强烈。
早上,当他天不亮就起床时,其他三个人都还在梦乡里。他轻手轻脚地洗漱完毕,背上书包准备去图书馆。
中午,他从图书馆回来,发现宿舍里热闹非凡。王涛和赵鹏正在激烈地讨论着昨晚的欧洲冠军杯,为曼联和拜仁哪个更强而争得面红耳-赤。他们看到李明盛,热情地招呼他:“明盛,快来评评理!你觉得索尔斯克亚那个绝杀,是不是越位了?”
李明盛愣了一下,他上一世是个铁杆球迷,但此刻,他脑子里却完全没有关于足球的任何念头。他只能尴尬地笑了笑:“我……我没看。”
“靠,这么经典的比赛你都不看?”王涛一脸不可思议。
晚上,宿舍里的话题,又转向了女生。赵鹏神秘兮兮地宣布,他搞到了外语系系花的课表,准备策划一场偶遇。室友们立刻来了兴致,纷纷为他出谋划策。
“你应该假装不经意地把书撞掉在地上!”
“不行,太老套了!你应该直接上去问她,同学,我觉得你很像我未来的女朋友!”
他们闹作一团,然后把话题抛给了沉默的李明盛:“哎,明盛,你觉得哪种方法好?”
李明盛看着他们那一张张因为青春而兴奋的脸,心中却是一片死水。他想起上一世,自己也曾为了追求一个女孩,做过无数这样幼稚而可爱的事情。但现在,他那颗四十岁的心,早已被生活的风霜磨砺得粗糙不堪,再也无法为这种纯粹的悸动而跳动了。
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混入羊群里的、苍老的牧羊人。
他只能再次选择沉默和疏离。
这种沉默,让他在宿舍里,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异类。室友们虽然没有排斥他,但彼此间的共同语言,确实越来越少了。他成了一座喧闹中的孤岛。
但李明盛并不感到难过。他知道,这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。他需要这种孤独,来完成对自己的重建。
他将图书馆,变成了自己的修行道场。
他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作息。每天早上六点起床,六点半准时出现在图书馆门口,成为第一个进去的人。晚上十点闭馆,他最后一个离开。他选择的位置,永远是三楼最偏僻的、靠着工具书架的那个角落。那里人最少,也最安静。
他的修行,充满了一种近乎偏执的仪式感。
他把所有专业课本,按照知识体系的底层到顶层,重新排了序:《离散数学》、《C语言程序设计》、《数据结构》、《汇编语言》、《计算机组成原理》、《操作系统》、《计算机网络》、《编译原理》。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重修计划,要将这八门核心课程,彻底吃透。
他学习的方式,也不再是简单的阅读和记忆。
学《数据结构》时,他不仅仅是看懂了红黑树的五条性质,而是买了厚厚一沓草稿纸,亲手将每一个插入、删除操作可能引发的旋转和变色,都画了一遍又一遍,直到形成肌肉记忆。
学《操作系统》时,他不再满足于背诵“进程的五个状态”,而是去下载了Linux 0.11版本的源代码。那是最早期的、只有两万多行代码的Linux内核,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他一句一句地去读那些汇编和C语言写成的、最底层的代码,去亲眼看一看,一个进程是如何被创建的,CPU的时间片是如何轮转的,内存是如何被分配和回收的。当他第一次,在代码里找到那段著名的“switch_to”宏定义,并理解了它如何巧妙地利用堆栈,完成了进程上下文的切换时,他激动得浑身颤抖。那是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、窥见事物本质的巨大喜悦。
学《计算机网络》时,他用一个叫“WireShark”的抓包工具(当然,是他凭记忆找到的99年某个简陋的替代品),去捕捉自己每一次上网时产生的数据包。他亲眼看着一个HTTP请求,是如何被层层封装,加上TCP头、IP头、以太网帧头,然后发送出去;又看着返回的数据包,是如何被层层解包,最终在浏览器里,渲染成一个网页。
这个过程,对他而言,是一种坐忘。他忘记了自己重生者的身份,忘记了深圳的惨败,忘记了对财富的渴望。他的整个世界,都沉浸在了这些由0和1构成的、冰冷而又滚烫的底层逻辑里。他的心,前所未有地,静了下来。
他的变化,引起了图书馆管理员周老师的注意。周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、即将退休的老太太,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。她见过无数的学生,有考前通宵的,有谈情说爱的,但像李明盛这样,日复一日,风雨无阻,像个苦行僧一样学习的学生,她还是第一次见。
有一次,李明盛因为钻研一个死锁的问题,忘了闭馆时间。当周老师拿着钥匙准备锁门时,才发现角落里还有他一个人。
“同学,闭馆了。”
李明盛这才如梦初醒。他不好意思地收拾东西。
周老师看着他那写满了密密麻麻代码和图表的草稿纸,忍不住说道:“小伙子,学习是好事,但也要注意身体。我看你最近,人都瘦了一圈。”
“谢谢老师,我会注意的。”
从那以后,周老师偶尔会给他带个自己家里做的茶叶蛋,或者提醒他天冷了多穿件衣服。这种来自陌生人的、朴素的关怀,让李明盛那颗孤寂的心,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温暖。
他就像一个饥饿了很久的人,扑在知识的海洋里,疯狂地汲取着养分。这个过程,对他而言,是一种修行。
他不再去想什么商业模式,不再去考虑什么融资。他通过这种方式,强迫自己忘记那个在深圳惨败的、自以为是的李明盛。他要通过重建自己最底层的知识体系,来重塑自己那颗已经破碎不堪的内心。
这个过程,是痛苦的,也是平静的。
他开始享受这种纯粹的、为了求知而学习的快乐。这是他上一世在KPI的重压下,早已失去的能力。在图书馆那个安静的角落里,时间仿佛都变慢了。他能听到的,只有自己翻动书页的沙沙声,和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。
他的心,前所未有地,静了下来。
他的变化,室友们都看在眼里。
“明盛最近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?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?”赵鹏私下里问王涛。
“谁知道呢?从上次请假回来就一直这样。不过也好,总比之前天天神神叨叨地念叨什么‘社交革命’强。”王涛耸了耸肩。
只有张伟,在某天晚上,看到李明盛草稿纸上画着一个复杂的B+树结构时,眼中闪过了一丝异样的光芒。他什么也没问,只是默默地把自己一本注解版的《算法导论》放在了李明盛的桌上。
李明盛看到了,他对张伟点了点头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在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理论修行后,李明盛开始感到一种技痒。他需要通过实践,来验证和巩固自己的所学,更重要的,是重建自己那已经跌入谷底的自信。
他没有再去想什么宏大的项目。他开始从身边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做起。
第一个练手项目,源于室友王涛的抱怨。学校的公共选修课名额有限,每次网上选课,都像一场战争。手速慢的,热门的课程瞬间就被抢光了。
“妈的,那个《电影鉴赏与拉片分析》,我又没抢到!”王涛愤怒地捶着桌子。
李明盛看着那个简陋的、基于表格提交的选课网页,心中一动。他花了一个晚上,用C语言写了一个小小的命令行脚本。这个脚本可以模拟浏览器的POST请求,以毫秒级的速度,不断地向服务器提交选课申请。
第二天,当下一轮选课开始时,他把脚本交给了王涛。“你把想选的课的ID填进去,然后运行这个就行了。”
王涛半信半疑。但当他运行脚本后不到一秒钟,屏幕上就显示“选课成功”时,他整个人都惊呆了。
“我操!明盛!你……你是神仙吗?!”王涛抱着李明盛,激动得又叫又跳。
这件事,很快就在宿舍楼里传开了。不断有人来找李明盛,求他帮忙抢课。李明盛来者不拒,但他有一个条件:每成功抢到一门课,对方要请他吃一顿食堂的饭。
就这样,在接下来的两周里,李明盛几乎没花过一分钱饭钱,还顺便把学校各个食堂的招牌菜都尝了个遍。
这个小小的成功,意义非凡。它没有带来财富,却给李明盛带来了比在深圳时更真实、更踏实的成就感。他第一次,用自己亲手敲下的代码,为身边的人,解决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。他的自信,像一颗种子,在这片坚实的土壤里,重新开始发芽。
接着,他又做了第二个玩具。他发现大家经常去校外的盗版影碟店租VCD,但片子质量参差不齐,还经常租到重复的。于是他花了一个周末,写了一个极其简陋的网页。他把自己和室友们看过的所有影碟,都录入进去,包括片名、导演、主演,以及一句简单的“推荐”或“不推荐”的评语。
他把这个“302宿舍影碟数据库”的地址,贴在了宿舍的门上。没想到,很快就有隔壁宿舍的人跑来,要求把他们的影碟也加进去。慢慢地,整个楼层的男生,都开始使用这个小小的网站。
这些微小的、看似无意义的实践,像一次次精准的康复训练,让李明盛那双因为好高骛远而残疾了的腿,重新学会了如何在现实的土地上行走。
在完成了这些技术练手,并重建了基本的自信后,李明盛才重新把目光,投向了那个更广阔的平台——学校的BBS。
但这一次,他的视角,已经完全不同。
他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产品设计者,而是一个谦卑的人类学观察家。
他没有急着去构思任何产品。他花了整整两周的时间,每天晚上都泡在BBS上。他什么也不做,就是潜水,观察。
他观察“十大热门话题”里,大家都在讨论什么。他发现,除了对国家大事的讨论,被顶得最高的话题,永远是关于“食堂的菜又涨价了”、“某某老师是个杀手”、“周末哪里有好玩的”这类最贴近校园生活的话题。
他观察“跳蚤市场”版块。他发现,交易最频繁的,不是随身听、游戏机这类大件,而是二手书、二手自行车、暖水瓶这类生活刚需品。他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:每到期末,出售二手教材的帖子就会暴增;而每到毕业季,甩卖所有家当的帖子则会刷屏。这背后,是清晰的、周期性的用户行为模式。
他观察“兼职实习”版块。他发现,最受欢迎的,不是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公司实习,而是学校周边那些派发传单、家教这类可以立刻拿到现金的短工。这说明,学生群体对即时回报的需求,远大于对长远发展的规划。
他甚至去观察“鹊桥”版块(交友版)。他发现,发帖征友的,男生远多于女生。而女生的帖子一旦出现,下面瞬间就会有几十上百条回复,其中大部分都是毫无营养的吹捧和插科打诨。这背后,是这个时代典型的狼多肉少的社交生态。
他把这些观察,都仔仔细细地记录在一个本子上。他画出了不同版块的用户活跃时间曲线,分析了高点击率帖子的标题特点,甚至还统计了不同类型交易的平均成交周期。
他感觉自己不像是在看一个网站,而是在观察一个复杂而有趣的、正在自我演化热带雨林”。
当他积累了厚厚一本的观察笔记后,那个关于“校园信息角”的想法,才最终,清晰地、完整地,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。
它不再是某天下午在图书馆里的一次偶然的灵光一现。它是基于长达数周的、对数千个样本进行观察和分析后,得出的一个必然的、水到渠成的结论。
这个结论就是:在当前阶段,BBS用户最核心、最未被满足的痛点,不是社交,而是信息效率。
人们不是不想交朋友,而是在交朋友之前,他们更迫切地,想先解决卖掉一本旧书、找到一份兼职、租到一间合适的房子这些更基本、更现实的生存问题。
想通了这一点,李明盛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。
他终于明白了,为什么他之前的社交网络会失败。因为他试图让一群还在为填饱肚子而奔波的人,去欣赏一幅关于诗和远方的画。
时机不对,一切都不对。
而“校园信息角”,就是为现在这群饥肠辘辘的人,递上的一份热腾腾的、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盒饭。
他没有立刻去找人,也没有再写什么商业计划书。
他回到自己的座位,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全新的本子,在第一页,郑重地写下了五个字:
“校园信息角”
这个名字,没有革命,没有未来,只有朴素和实用。
然后,他开始写下这个产品的第一版需求文档。他写得非常慢,非常仔细。每一个功能点,都源于他那些观察笔记里的真实数据和用户行为分析。
那个晚上,李明盛时隔一个多月,第一次在闭馆铃声响起前,就离开了图书馆。
他没有回宿舍,而是直接去了计算机系的公共机房。机房里,张伟正戴着耳机,全神贯注地敲着代码。
李明盛没有像上次那样,用一堆华丽的辞藻去说服他。他只是静静地站在张伟身后,等他打完最后一行代码,按下了保存。
“张伟,”李明盛的声音平静而沉稳,“我这儿有个东西,你想不想看看?”
他没有递上一份画满框框的蓝图,而是将那本写满了需求和思考的、朴实无华的本子,递了过去。
张伟疑惑地接过本子,翻看了起来。
他的眉头,一开始是舒展的,然后微微皱起,似乎在思考技术实现,接着又舒展开。他看得非常认真,足足看了十分钟。因为本子里的内容,不是空想,而是由一行行逻辑和一条条推导构成的,那是一种他最熟悉、也最尊重的语言。
看完后,他合上本子,推了推自己的黑框眼镜,抬起头,看着李明盛。他的眼神里,没有了之前的警惕和怀疑,而是多了一丝纯粹的、属于技术人员的、看到一个有趣且可行的问题的兴奋。
他只说了四个字:
“这个,能做。”
李明盛笑了。
他知道,自己重生后的下半场,在这一刻,才真正地,开始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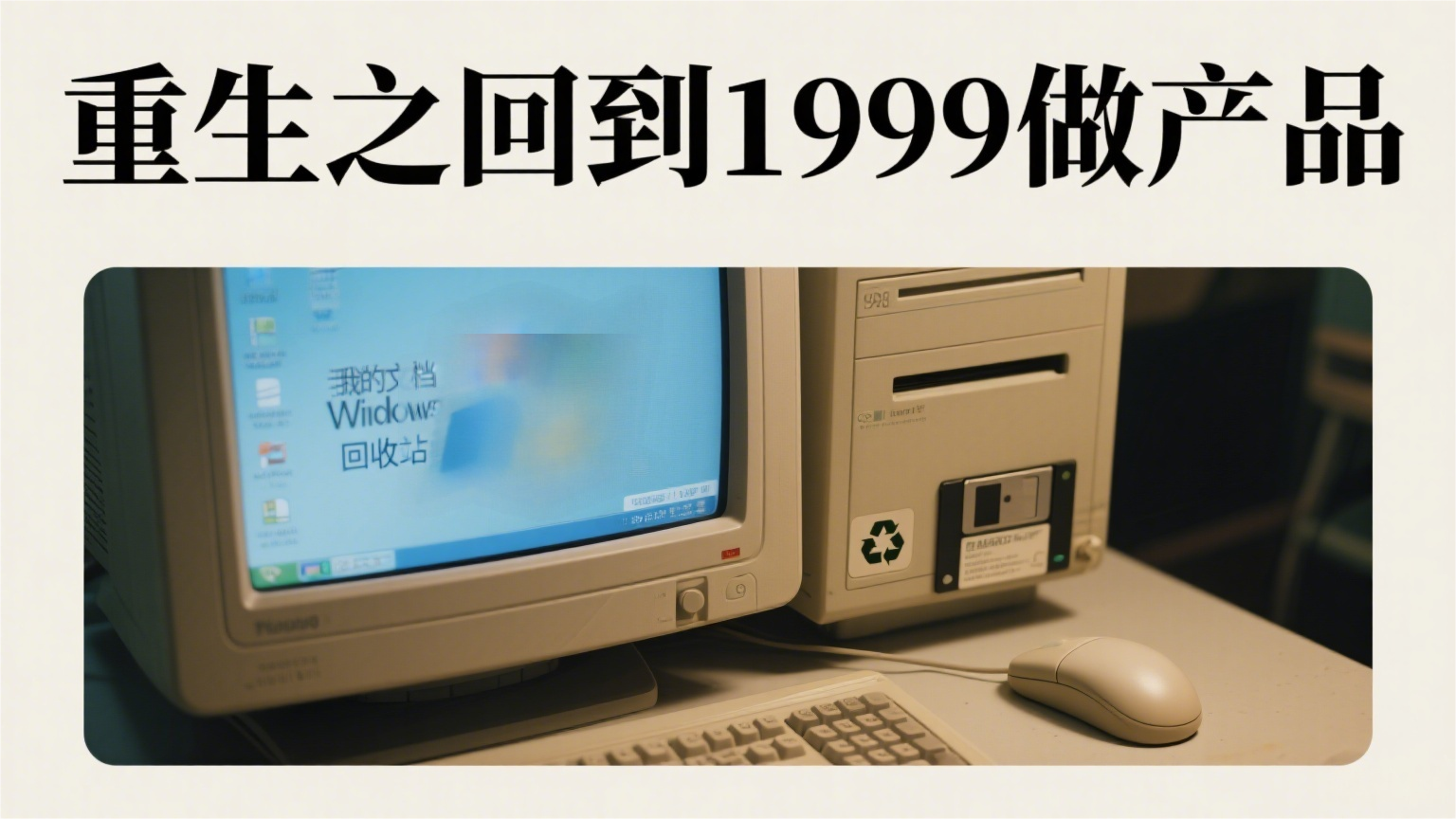
发表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