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上的列车,载着的是理想;南下的列车,装满的是欲望。
这是1999年,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。北京,是文化和政治的中心,是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们激扬文字、指点江山的地方。而深圳,那个南海边由一个小渔村迅速崛起的奇迹之城,则是所有草根、所有野心家、所有渴望用双手改变命运的人们心中的淘金圣地。
李明盛坐在开往深圳的T15次列车的硬座车厢里,心中默念着这句话,但他觉得,自己与这两种人都不同。他既有北上的理想——他要用自己超越时代的认知,去创造一个伟大的产品,改变未来的社交格局;他也有南下的欲望——他要借此实现财富自由,将上一世所有的不甘与平庸,彻底踩在脚下。他是一个怀揣着理想的淘金者,一个看透了未来的赌徒。
这趟旅程,他没有告诉宿舍里的任何人。在他们眼里,李明盛自从挑战杯失败后,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,整天不是泡在图书馆,就是对着电脑发呆。没人知道,他那看似平静的外表下,正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南征。他只是对辅导员请了个假,理由是“家中有急事”。这个借口让他自己都觉得有些讽刺,或许,去追寻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,确实是他内心深处最焦急的家事。
火车是绿皮的,像一条巨大的、疲惫的铁龙,喘着粗气,缓缓驶出北京西站。车厢里拥挤而嘈杂,构成了一幅流动而鲜活的九十年代末浮世绘。空气中混合着汗味、脚臭味、方便面调料包的香味以及劣质香烟的辛辣味,形成一种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、令人永生难忘的旅途气息。过道上都挤满了没有座位的乘客,他们或坐或蹲在自己的行李上,目光或茫然或充满希冀地望着窗外,将整个车厢塞得水泄不通。
李明盛的位置靠窗,这是他特意加了五块钱从一个票贩子手里换来的。他需要一个能让他思考和观察的角落。他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华北平原,心中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烦躁。相反,他享受着这种混乱和嘈杂。这人间烟火的真实感,让他觉得自己正牢牢地抓着这个时代。他甚至有些贪婪地呼吸着这污浊的空气,因为这空气里,有他逝去的、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味道。
他的背包里,没有几件换洗衣物,却塞着那份被他重新打印和装订了十几遍的《校园社交网络商业计划书》。封面用的是最醒目的加粗黑体,标题被他改了又改,最终定格为——《连接未来:引爆中国高校互联网社交革命》。他用“革命”这个词,是因为他坚信,自己的想法对于这个时代而言,就是一场彻底的颠覆。他甚至还在扉页上,引用了一句凯文·凯利的话——未来已经到来,只是尚未流行。当然,他知道凯文·凯利此刻可能还没说过这句话,但这并不妨碍他借用未来的智慧来装点门面。
他的对面,坐着一个皮肤黝黑、穿着的确良衬衫的河南青年栓子,一心只想着去电子厂挣钱盖房。而在他的斜对面,则坐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,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微缩社会样本。
一个是约莫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,穿着一身半旧的灰色中山装,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从上车开始就一直在聚精神会神地读一份《人民日报》。他的坐姿笔挺,茶缸放在桌上,盖子盖得严严实实,透着一股老派干部的严谨。他叫冯建国,是在国家某部委工作的老科员,这次去深圳是参加一个关于“国有企业信息化改革”的研讨会。
另一个则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,穿着一件时髦的POLO衫,手腕上戴着一块明晃晃的金色手表,虽然李明盛一眼就看出是块假劳力士。他操着一口浓重的粤语普通话,正在大声地打着电话,电话那头似乎是什么生意伙伴。他叫梁浩,一个在华强北倒腾电子元器件的个体户。
火车开动后不久,矛盾就爆发了。梁浩又接起一个电话,声音更大了,唾沫横飞,讨论着什么VCD解码芯片的差价。“喂?阿强啊!那批货明天一定要到啊!……你放心啦!深圳这边市场大得很,有多少都能吃得下!……价格?价格好说啦,见面再谈!”他挂掉电话,意气风发地扫视了一下周围,目光里充满了对这节慢悠悠的绿皮车厢的鄙夷。
读报纸的冯建国终于忍不住了,他放下报纸,扶了扶眼镜,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:“这位同志,请你小点声,这是公共场合。”
梁浩斜了他一眼,嗤笑道:“阿叔,现在是市场经济啦,我谈的是生意,是时间,是金钱!你懂不懂啊?你不打电话,不代表别人不忙啊。”
“在公共场合保持安静,是基本的社会公德,这和市场经济没关系。”冯建国寸步不让,身上那种体制内的威严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。
眼看两人就要吵起来,周围的人纷纷投来目光。李明盛此刻内心是偏向梁浩的。在他看来,冯建国代表了他所鄙视的、邓教授那种僵化保守的思维,而梁浩身上那种追逐效率和财富的原始冲动,虽然粗鄙,却充满了生命力,更接近深圳的精神。
他甚至想开口帮腔,说几句“效率优先”之类的话。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,旁边一个一直沉默着的、看起来像个退伍军人的中年大哥发话了,声音洪亮:“都少说两句!出门在外,都不容易。老板,你声音是大了点。大叔,您也消消气。”
一场冲突就这么被化解了。李明盛没有说话,但他心里却第一次有了一丝异样的感觉。他发现,这个真实的世界,并非像他想象中那样,可以用先进与落后的标签简单粗暴地一分为二。这里面,还有公德、人情这些他重生以来从未认真考虑过的东西。
入夜,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。李明盛毫无睡意。他对面的栓子已经靠着行李睡着了,发出了轻微的鼾声。梁浩也收敛了许多,正拿着一个小本子奋笔疾书地记着什么。
就在这时,冯建国忽然开口了,他看向李明盛,目光落在他腿上那份商业计划书的封面上。
“同学,你是北京的大学生吧?”
“是的,大叔。”李明盛有些意外。
“去深圳,也是去做‘互联网’?”冯建国显然听到了他之前和栓子的对话。
“嗯,算是吧。”李明盛整理了一下思路,觉得这是一个预演的好机会,一个说服保守派的机会。
“我儿子,也在搞这个。”冯建国叹了口气,眼神里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感情,“他在邮电部下面的一个研究所,天天念叨什么‘数据’、‘信息高速公路’。我听不懂,但我总觉得,这东西,有点虚。”
“虚?”这个评价让李明盛皱起了眉头,他决定发起反击,“冯叔叔,您觉得什么是‘实’呢?是钢铁,还是粮食?”
“对,就是这些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东西。”冯建国很认真地说道,“我们这一代人,信奉的是这些。我搞了一辈子水利工程,修一座大坝,就能灌溉几十万亩良田,能让几百万老百姓喝上水。这是实实在在的功绩。可你们这个互联网,在电脑上点来点去,财富就产生了?我总觉得不踏实。它不生产粮食,也不生产钢铁,它生产什么?”
李明盛清了清嗓子,开始了他准备已久的布道:“冯叔叔,您说的没错,互联网本身不生产钢铁和粮食。但是,它可以让钢铁厂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买家,减少库存,提高资金周转率;它可以让农民知道全国哪个地方的粮价最高,把粮食卖出好价钱。它生产的,是‘效率’,是‘信息’。在未来的时代,信息和效率,就是最大的财富,它的价值,远超钢铁和粮食。”
这番话,让旁边的梁浩都听得抬起了头,眼中露出了一丝兴趣。
冯建国沉思了片刻,却摇了摇头:“你说的这些,听起来很美好。但根据我的了解,现在大部分搞互联网的公司,都在烧钱,都在亏损。报纸上都说了,这叫‘泡沫’。一个不赚钱的东西,怎么能叫财富呢?”
“那是前期的投入!”李明盛急于辩护,“任何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前期的投入!铁路、公路,在建成之前不也一样是纯投入吗?我们这是在修建一条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,一旦建成,上面跑的每一辆‘车’,都能创造价值!”
“说得好!”梁浩忽然插话了,他兴奋地对李明盛说,“兄弟,你这个‘信息高速公路’的比喻,我钟意!没错,冯大叔,我们现在干的事,就是在修路!路修好了,我们这些跑运输的,才能发大财嘛!”他显然把自己代入到了跑运输的角色里。
李明盛得到了盟友,更加自信了。
但冯建国却依然不为所动,他看着李明盛,问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:“好,就算你说的都对。那我想问问你,同学,你这份计划书上写的‘社交革命’,又是什么?修路,是为了运货。你这个‘社交’,运的是什么?是人与人之间的闲聊吗?这种东西,也能创造价值?”
这个问题,直指李明盛项目的核心。
“运的是关系!”李明盛激动地说道,“我们把现实中的人际关系,搬到网络上,形成一个巨大的、相互连接的网络。在这个网络里,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将是前所未有的。比如,一个好的产品,可以通过好友之间的信任推荐,迅速引爆。这就是价值!它改变的是营销模式,是信息传播的模式!”
“哦?”冯建国扶了扶眼镜,眼神变得锐利起来,“听起来,倒像我们以前搞的人传人。那如果传播的是谣言呢?是错误的信息呢?谁来监管?谁来负责?在现实里,你说错话了,要负责任。在网络上,大家躲在一个名字后面,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?你这个‘革命’,会不会把社会搞乱?”
李明盛愣住了。他发现,自己又绕回了邓教授和挑战杯评委们提出的那个管理和安全的原点。他以为商业社会不会关心这些,但一个老派的干部,却如此敏锐地指出了他模式里最大的社会性风险。
“我们……我们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来规避这些问题……”他的回答显得苍白无力。
冯建国摇了摇头,不再与他辩论,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:“年轻人,创新是好事,但不要忘了‘责任’两个字。任何技术,如果脱离了责任的缰绳,最终都可能变成一匹毁掉一切的野马。”
说完,他便闭上眼睛,靠在椅背上假寐。
这次长谈,像一场预演,提前暴露了李明盛思想中的所有弱点。他原以为自己是降维打击,结果却被一个老干部用最朴素的价值观问得哑口无言。他心中的那团火,第一次被浇上了一盆来自现实的冷水。
三十多个小时的颠簸后,火车终于缓缓驶入了深圳站。
当李明盛背着包,随着拥挤的人潮走出车站的那一刻,一股混杂着海洋咸湿气息的热浪,夹杂着无与伦比的喧嚣,扑面而来。他拒绝了所有拉客的司机和旅店老板,凭着记忆,坐上了一辆颠簸的中巴,来到了深南中路附近的岗厦村。
走进村子,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狭窄的巷子里,握手楼密密麻麻,几乎遮蔽了天空。头顶是蜘蛛网般杂乱的电线,上面还挂着不知谁家滴水的衣服。脚下是湿滑的青苔路面,混合着生活垃圾渗出的污水,散发着一股酸腐的气味。
招待所的老板是一个精瘦的潮汕人,他递给李明盛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,带他上了三楼。房间很小,只有五六平米,一张吱呀作响的铁床,一张桌面已经翘皮的桌子,和一台扇叶上积满灰尘的电风扇。卫生间和浴室是公用的,在走廊的尽头。
“二十块一晚,押一付一。身份证押这儿。”老板言简意赅。
李明盛放下行李,想去洗把脸。公共卫生间里,一股浓烈的氨水味扑面而来,让他几欲作呕。水龙头是坏的,一直在滴水,下面的水槽里积满了黄色的水垢。他忍着不适,匆匆冲了把脸。
回到房间,墙壁很薄,他能清晰地听到隔壁房间里,一个女人正在用带着哭腔的方言打电话:“……妈,我钱都寄回去了……我这里挺好的,老板对我不错……放心吧,我过年……过年争取回去……”
这声音,让李明盛的心里莫名地一酸。但这一次,他没有再把自己摆在救世主的高度。他只是觉得,自己和这个看不见的女孩,以及火车上那个叫栓子的青年,都是这座巨大城市里的燃料,燃烧自己,去点亮远方家人的希望。
饥饿感袭来。他走出招待所,在巷子里寻找食物。一家隆江猪脚饭的小店吸引了他。招牌油腻,灯光昏暗。他点了一份最便宜的五块钱的快餐。老板娘从一个巨大的不锈钢桶里,舀了一勺米饭,又从几个大盆里,随意地舀了两勺菜,一勺是炒冬瓜,几乎看不到油水,另一勺是麻婆豆腐,只有几粒可怜的肉末。
他端着餐盘,在油腻的桌边坐下,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味道谈不上好,但米饭管饱。邻桌,坐着几个穿着工厂制服的年轻女孩,她们一边吃饭,一边兴奋地讨论着周末要去世界之窗玩。她们的脸上,洋溢着对未来最纯粹的憧憬,那是生活的疲惫无法掩盖的光。
李明盛忽然觉得,自己那份商业计划书里描绘的用户,不再是一个个冰冷的数据和画像,而是变成了眼前这些鲜活的、有血有肉的人。他那个连接人的伟大理想,在这一刻,被拉到了最卑微的现实里。
在深圳的前两天,高交会还没正式开始。李明盛没有浪费时间,他想先了解一下这座城市的脉搏。他揣着地图,用双脚丈量着这片土地。他去了当时深圳的电子心脏——华强北。
彼时的华强北,还不是后来的中国电子第一街,而是一个巨大而混乱的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。赛格电子城里,密密麻麻的柜台如同蜂巢,每一个柜台后面,都坐着一个精明的生意人。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,只有最原始的商业逻辑:低买高卖。人们讨论的不是模式,而是这批货能赚几个点。
李明盛在这里看到了火车上遇到的梁浩。他正站在一个柜台前,和老板为了一毛钱的差价,争得面红耳赤。看到李明盛,他有些尴尬地笑了笑,然后把他拉到一边,递给他一支烟。
“兄弟,你也来这边逛?”
“随便看看。”
“怎么样?找到你的‘信息高速公路’了吗?”梁浩调侃道。
李明盛苦笑了一下:“路还没找到,收费站倒是挺多的。”
梁浩哈哈大笑:“兄弟,我跟你说,别信那些虚头巴脑的。在深圳,先生存,再发展。你看我,前几年刚来的时候,睡在仓库里,一天只吃两顿饭。现在,虽然发不了大财,但每个月也能赚个万把块。靠的是什么?就是脸皮厚,腿脚勤,脑子活!”
他指着那些繁忙的柜台说:“这里每一个人,都比大学里的教授更懂市场。因为市场错了,教授最多是丢点面子。我们要是看错了市场,那可是要亏掉底裤,卷铺盖回老家的!”
梁浩的话,像一把锉刀,再次打磨着李明盛那颗被理论包裹得过于光滑的心。
在岗厦村的几个晚上,李明盛几乎夜夜失眠。电风扇的噪音,巷子里彻夜不息的喧哗,以及隔壁房间不时传来的夫妻吵架声、婴儿啼哭声,都让他无法入睡。他躺在坚硬的铁床上,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因为潮湿而 oluşan的霉斑,脑子里反复回想着火车上冯建国的话,和华强北梁浩的话。
两种截然不同,却又都无比真实的声音,在他脑海里交战。他发现,自己那个看似完美的商业计划,既无法满足冯建国对社会责任的要求,也无法满足梁浩对现金为王的渴望。
他那份计划书,就像他自己一样,悬在了半空中。
高交会开幕的日子终于到了。
李明盛郑重地将那份商业计划书放进文件袋。几天的底层生活,并没有磨灭他的希望,反而让他有了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感。他觉得,自己已经看透了现实的残酷,现在,他要去寻找能够理解他理想的同类。
展馆内人山人海。李明盛的目标很明确——寻找VC。他花了一天的时间,摸清了几个重要论坛的日程安排。他发现,有一个“互联网创新项目路演”的分论坛,虽然不对普通观众开放,但安保似乎并不严格。
第二天,他起了个大早,换上自己唯一的一件白衬衫,甚至还花两块钱在村口让老师傅用发蜡抓了个发型。他借了一位同住招待所的、在华强北卖手机的大哥的工牌,挂在胸前,然后深吸一口气,大摇大摆地走向那个分论坛的入口。
门口的保安扫了一眼他胸前的牌子,又看了看他那故作镇定的学生脸,犹豫了一下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李明盛急中生智,指着里面大声说:“王总让我进去拿份材料!”
保安或许是被他这股理直气壮的劲头唬住了,竟然侧身让他进去了。
李明盛的心狂跳不已。他成功混了进来!
会场里坐着的,都是西装革履的业内人士。他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,一边听着台上的人用各种专业术语介绍着自己的项目,一边用鹰隼般的目光,在台下的嘉宾席里寻找着自己的猎物。
他很快锁定了一个目标。那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年轻的男人,约莫三十岁上下,胸牌上写着“深港创投 – 投资经理 – 赵德光”。这个公司的名字他上一世没听过,说明不是顶级VC,但也正因为如此,或许门槛会低一些,更愿意听一个大学生的想法。
路演结束后,有一个短暂的茶歇时间。李明盛立刻抓住机会,端着一杯免费的速溶咖啡,走到了赵德光的面前。
“赵经理,您好!我是来自北京邮电大学的创业学生李明盛,我这里有一个项目,可能会颠覆现有的BBS模式,您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听我讲一下吗?”
赵德光推了推金丝眼镜,上下打量了他一下,点了点头:“可以,不过我只有十分钟。”
两人走到了一个人少的角落。李明盛激动得手心冒汗,他立刻打开自己的商业计划书,开始了演说。这一次,他吸取了与冯建国对话的教训,特意强调了项目的社区管理和正向引导功能。
赵德光耐心地听着,等他讲完,才缓缓地开口。他没有立刻否定,而是像一个老师一样,开始引导性地提问。
“李同学,你的计划书我看完了。逻辑很自洽,很有激情。我们先不谈那些宏大的,我们来聊聊细节。你第四页提到,项目启动需要三十万资金,其中服务器和带宽费用占了二十万。这个数据,你是怎么算出来的?”
李明盛一愣,这个数据是他根据后世的经验,拍脑袋估算的。他支吾道:“这是根据……我们预估的第一年十万用户的并发访问量,以及数据存储量来计算的……”
“哦?”赵德光嘴角微微上扬,“那你知不知道,1999年,在中国电信租用一条2M的带宽,一年的费用是多少?IDC机房一个标准机柜的托管费又是多少?按照你的用户模型,十万用户每天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上传一张100K的照片,一天就是1G的流量,一个月就是30G。你这二十万里,连带宽的钱都不够付。”
李明盛的脸瞬间就白了。他对这个时代的基础设施成本,一无所知。
赵德光没有停,继续发问:“你第七页说,你的核心优势是‘基于真实关系的病毒式营销’。那你有没有做过市场调研?中国大学生的宿舍,有几台电脑?有多少人能随时上网?大部分人上网还要去网吧,一个小时三块钱。你觉得,他们会花这个钱,在你的网站上‘分享生活’吗?你的‘病毒’,传播的媒介是什么?靠嘴吗?”
“还有,你第十页的盈利模式。你说参考AOL,做会员增值服务。你知道AOL的增值服务是什么吗?是捆绑了独家新闻内容、股票信息和电子邮件服务。这些,你有吗?你说参考Yahoo,做广告。你知道品牌广告主投放广告,需要看什么数据吗?他们需要看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用户画像报告、消费能力分析。这些,你又怎么提供?”
“另外,你的用户定位是大学生,对吧?这个群体的特点是高度同质化、消费能力弱,而且流动性极强,毕业就流失了。你如何解决用户生命周期过短的问题?”
“你说要形成网络效应壁垒,但校园社交的壁垒其实很低。清华的学生,为什么要关心北大的学生在分享什么?你的‘关系链’,很可能只是一个个孤立的局域网,无法形成真正的全国性网络。你怎么看?”
“最关键的一点,你说前期免费,靠后期增值服务和广告盈利。但大学生群体是最价格敏感的用户,让他们付费的难度极高。至于广告,在没有证明你的用户具备消费潜力之前,没有任何一个品牌广告主会愿意为一群穷学生买单。你的盈利模式,在我看来,是一个悖论。”
赵德光的每一个问题,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,将李明盛那份看似华丽的商业计划书,解剖得体无完肤。他让李明盛清晰地看到,自己的整个构想,都建立在一片由想当然和未来记忆构成的流沙之上。
李明盛的额头渗出了冷汗。他上一世是做产品,是执行者,他很少从投资人这种上帝视角去审视一个商业模式的根本性缺陷。他脑子里那些关于Facebook成功的记忆,此刻完全无法用来回答这些针对中国国情和1999年现状的尖锐问题。
他支支吾吾,用一些“未来可以探索……”“我们可以通过运营手段……”之类的空话来搪塞。
赵德光看出了他的窘迫,微微一笑,他递给李明盛一张名片。
“想法很好,但太理想化了。回去把产业的上下游,把市场和用户,都研究透了再说吧。做生意,不是写科幻小说。”
李明盛拿着那张名片,感觉重如千斤。这次失败,是知识层面、专业层面的彻底溃败。他第一次发现,自己引以为傲的行业经验,在脱离了相应的时代背景后,是多么的不堪一击。
他失魂落魄地走出论坛会场,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戳破了的气球。他需要吃点东西来补充体力。他走出展馆,在外面一个卖盒饭的小摊上,买了一份最便宜的快餐。
他刚蹲在路边准备吃,旁边也蹲下来一个人。他转头一看,竟然是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金表男梁浩。
梁浩也认出了他,咧嘴一笑:“兄弟,这么巧!怎么样,你的‘革命’,成功了吗?拉到投资没?”
李明盛苦涩地摇了摇头。
“我就知道!”梁浩用筷子指了指展馆,“里面一大半都是跟你一样的大学生、知识分子,抱着个点子就想当老板。我告诉你,没用!”
他打开自己的饭盒,里面是丰盛的烧鹅,和李明盛的炒冬瓜形成鲜明对比。他夹起一块烧鹅,继续说道:“你知道我这两天在干嘛吗?我没去谈什么投资。我带着我的样品,直接去了华强北的几个大档口,请那些老板吃饭、桑拿。昨天晚上,就签下来一个五十万的单子!”
“五十万?”李明盛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“小意思啦。”梁浩得意地剔着牙,“我这人,不信什么计划书。我就信两样东西:订单和现金。有订单,银行都追着给你贷款。有现金,我就可以去压上游供应商的价。这生意,不就做起来了?”
他看着李明盛,语重心长地说道:“兄弟,听我一句劝。别总想着搞什么‘革命’。先想想,怎么能让你兜里这个月比上个月多出一百块钱。你什么时候能不吃五块钱的快餐,改吃我这种十五块的烧鹅饭了,你再来跟我谈‘模式’。”
说完,他三下五除二地吃完饭,拍了拍李明盛的肩膀:“我还有个饭局,先走了。你好自为之。”
梁浩的这番话,比赵德光的专业分析,带来的冲击力更大。那是一种来自最底层、最生猛的生存智慧,对学院派理论的无情嘲讽。它让李明盛感到一种深深的羞辱。他引以为傲的智力优势,在赤裸裸的现实面前,显得如此可笑和无力。
经历了双重打击,李明盛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。他像一个游魂一样,在会场里飘荡。他不甘心,他觉得一定还有人能理解他。
就在这时,他看到了那个改变他一切认知的场景。
在会场最不起眼的角落里,他看到了那个戴着眼镜的、文弱的年轻人——马化腾,和他的OICQ。
他站在不远处,静静地观察了很久。他看到马化腾不厌其烦地向每一个路过的人演示着OICQ的功能,声音不大,但很清晰。他看到有好几个像他一样的年轻人,对这个能免费聊天的小软件很感兴趣,还互相加了号码。
然后,他看到了那个投资人走过来,问出了那个致命的问题:“你这个东西,靠什么赚钱?”
当他听到投资人那句轻蔑的“不就是一个网络寻呼机吗?没意思”时,李明盛感觉自己的心脏,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地攥住了。
他看到投资人转身离去时,马化腾脸上那努力维持的笑容,瞬间垮塌了下来。那一闪而过的失望、无奈和疲惫,是如此的真实,如此的刺痛人心。
这一刻,李明盛脑海中所有关于腾讯未来帝国的辉煌记忆,与眼前这个窘迫、无奈的身影,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和撕裂。
他终于想通了。
赵德光代表了资本的理性,他要求商业逻辑的闭环。梁浩代表了市场的现实,他要求立竿见影的现金流。而被他们同时否定的马化腾,却代表了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——用户的需求。
马化腾可能回答不了赵德光关于盈利模式的诘问,也无法满足梁浩对现金流的渴望。但他和他的OICQ,解决了当时中国数百万网民最基本、最迫切的一个需求——免费、便捷的即时通讯。
先满足需求,活下去,把用户握在手里,再去谈商业,再去谈未来。
这才是1999年,中国互联网最根本的生存法则!
而自己呢?从头到尾,都在用一个2025年的结果,去强行套嵌1999年的过程。他既没有满足资本的理性,也没有迎合市场的现实,更没有像马化腾一样,去真正解决一个当下用户的真实需求。
他只是一个拙劣的、试图作弊的穿越者,却被现实的监考官,抓了个正着。
高交会闭幕的音乐响起了。工作人员开始清场。李明盛失魂落魄地随着人流,走出了展览中心。
深圳的夜,灯火辉煌,充满了机遇和梦想。但这一切,都与他无关了。他站在天桥上,看着脚下川流不息的车河,将那份被他寄予了无限厚望的商业计划书,一页一页地,撕得粉碎。纸屑,随风飘散,融入了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之中,无声无息。
他没有回招待所。那一夜,他在深圳的街头,游荡了整整一夜。
他从繁华的华强北,走到了寂静的荔枝公园。他看到深夜的大排档里,喝得酩酊大醉的生意人抱着头痛哭;他看到24小时便利店里,上夜班的女孩靠着货架打盹;他看到天桥下,蜷缩着席地而睡的流浪汉……
每一个画面,都在提醒他这个世界的真实与残酷。
他想起了上一世,自己刚毕业时,为了省钱住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,每天啃着馒头就咸菜,熬夜学习编程的日子。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做项目经理,因为一个BUG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,一个人在公司楼下哭了半个小时,然后擦干眼泪回去继续加班的夜晚。他想起了自己为了一个产品上线,连续一个月睡在公司,妻子送来的汤都凉了,他才有空喝上一口。
他上一世的成功,哪有什么捷径?全都是靠着一步一个脚印,用无数的汗水、泪水和不眠之夜,硬生生熬出来的。
可重生之后呢?他被那该死的先知身份冲昏了头脑。他看不起身边的一切,鄙视所有的规则,总想着一步登天。他变得浮躁、傲慢、眼高手低。
他以为自己是来降维打击的,结果却被这个时代,用最朴素、最坚硬的现实,教育得体无完肤。
凌晨五点,当东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,第一缕晨光照亮这座城市的时候,李明盛正坐在海边的礁石上。海风吹拂着他疲惫的脸,也吹走了他心中最后的迷雾。
他终于想明白了。
重生,不是让他来当一个无所不能的神,而是给了他一个机会,去重新当一次人。一个更踏实、更谦卑、更敬畏现实的人。
那条他以为金光闪闪的捷径,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前方,是一片望不到边的黑暗。但他心里,却又隐隐约约地,亮起了一丝微弱的光。那束光告诉他:回到原点,回到现实,回到身边,从解决一个最小的、最真实的问题开始。
先想办法,让自己和自己的产品,活下去。
他买了一张最晚回京的火车票,一张硬座。揣着兜里仅剩的十几块钱,他坐上了北上的列车。
来时,他意气风发,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他的脚下。
归时,他孑然一身,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丧家之犬。
但他的心里,却比来时,更加踏实。
当火车再次驶入北京站,他背着空空如也的背包,走出车站,看着北京九月微凉的秋风卷起地上的落叶。
他感觉,自己重生后的上半场,已经以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,结束了。
而下半场,将从他杀死那个自以为是的先知李明盛开始。
他要像一个真正的新生儿一样,重新开始学习,如何在这个时代里,蹒跚学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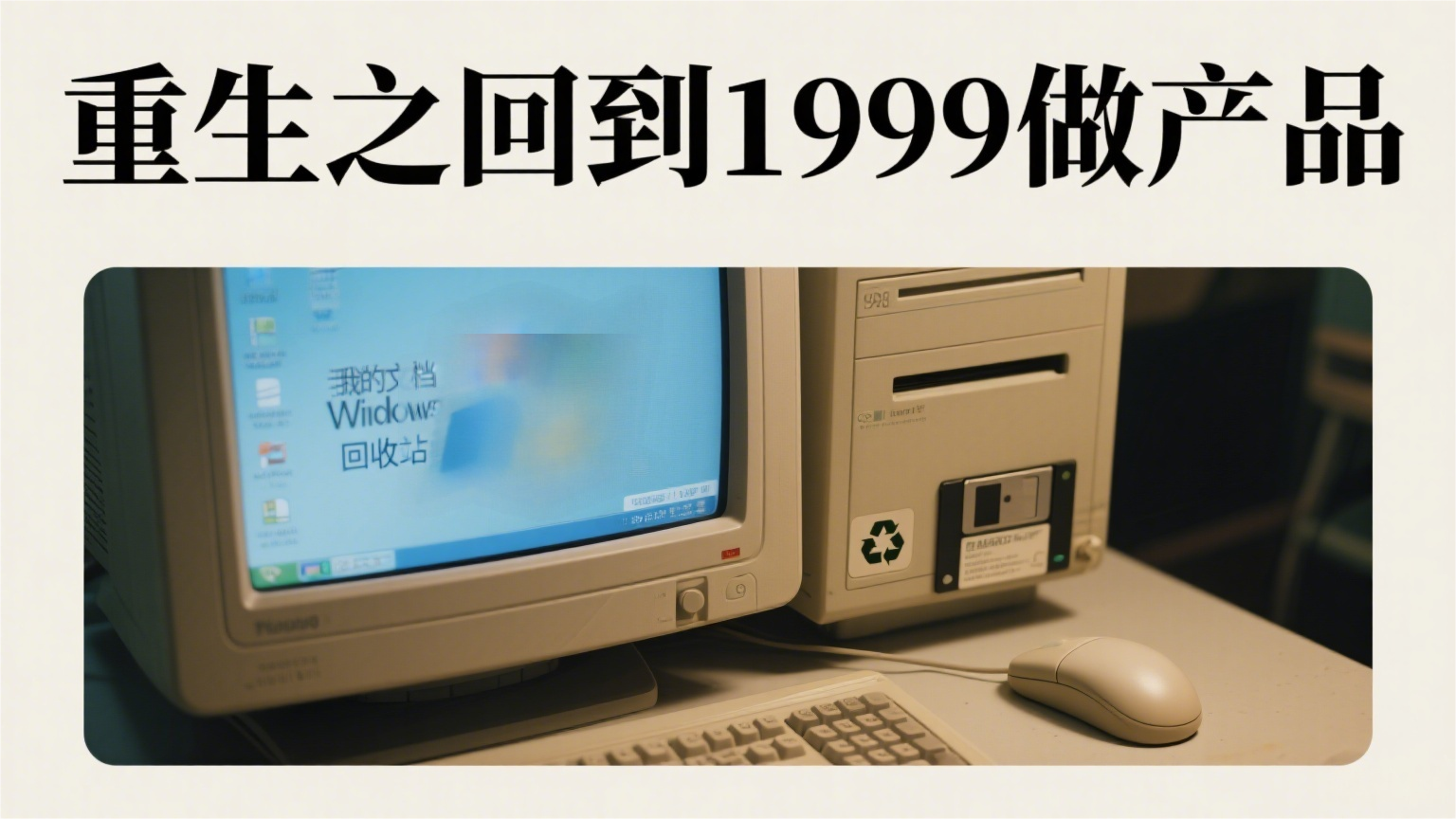
发表回复